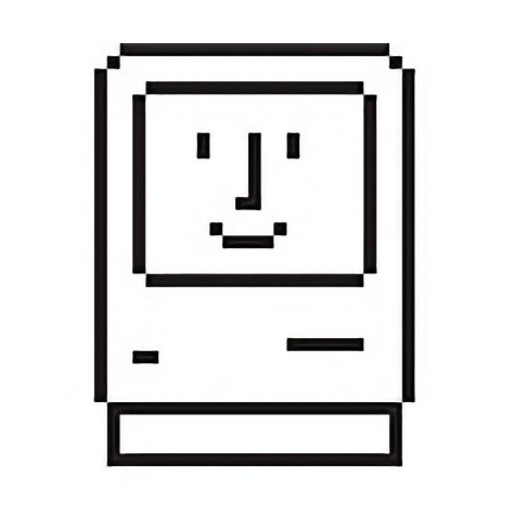看到路边被遗弃的空可乐罐,我想到生命与非生命的结局竟可以如此相似。如果人是机器,那么本可以无感于悲欢离合。然而进化出了如此丰富的感情,既让人着迷,又让人毁灭。人类社会从很大程度上来讲,乃是感情社会。人的受伤从很大程度上来讲,乃是感情受伤。
我并非一个善于捕捉并运用感情的人。像我这样的人,怎么会恋爱呢?可惜我还是很不争气地恋爱了。
我的女友——现在应该是前女友了——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。某一次,她上课坐在我身边。那节课我对黑板上的几道积分题十分关注,无瑕左顾。她静静地坐着,一句话不说。我用纸笔飞速演算,几分钟后便得出了答案。正当我长舒一口气,左边忽然传来一个微风般的声音:
“你做出来啦?”
我一眼便能注意到一个惊人的代数变形,然而却要扭头才能注意到她美丽的侧脸。
“噢……对……”
我失神地答道。她飘逸的长发犹如积分符号,妆容是平凡的,但不难看出五官精致可爱。不妨将视线稍作下移,她穿着的米白色衬衫令我舒心。因为假设其他的颜色也能使我舒心,则与我对素雅颜色的偏好相矛盾,我便不再是我了。回到她的面庞,注意到她的表情带有……期待?好奇?总之是善意的。
我稍往后靠一点,方便她看到我这张字迹潦草的稿纸。正如门捷列夫用潇洒的字迹完成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,我对这道题的答案也拥有充分的自信。她探过头看起来。在我眼前出现了两种由碳构成的积分符号,一种是笔迹,一种是发丝。最终她摇摇头,轻笑道:
“有点看不懂,不过很厉害的样子,佩服佩服!”
我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呢?我想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。当前,我应该礼貌地笑笑。如果我是一个情圣,那么此刻我会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认识美女的机会。然而主观上我对此并无兴趣,客观上也没有这样的技巧。
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一边听课做题,一边解答她偶尔的疑问。我尽量使我的叙述准确严谨,以免误人子弟。她每次都耐心听完,要么再补充问一句,要么就“嗯”一声,然后表示感谢;大多数情况下是后者。至于她听没听懂,实际上我并没有把握。
高数课是每周两节,此后的高数课,她一直坐在我旁边,像那天那样讨论问题。费曼曾说,如果你能将一项知识用你祖母也能听懂的语言教给她,那么你就真正掌握了它。虽然这位女生不是我祖母,但教她数学对我的学习益处颇多,是可以承认的。——对了,此后两周,我甚至都没有问她的名字,她也没有问我的名字。
“一起去吃饭吧?”她的一个邀请,为我们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章。
离开了课堂,我只好聊一些与数学无关的事,这就难免问到她的名字。她叫冯凌,和我同专业,但不同班。她侃侃而谈,我随声附和,沉闷的我总是这样扭扭捏捏。大概她可以从社交中获得能量,而我只能快速消耗能量。
我觉得她很幸福,有那么多有趣的朋友,还有广泛的兴趣爱好,平时喜欢游山玩水、看剧追番,见识广博,谈吐不俗。虽然我也常自诩乃至自欺是个很幸福的人,但给出的理由却经不起太多推敲。平心而论,我只是在一些方面有些小聪明的书呆子而已,我的生活振动与她相比多少缺了点谐波。
除了课堂上和她讨论数学,我并不太习惯私下与她相处。她说的大部分话题我都不感兴趣,但是她的善意使我很难拒绝和她共进午餐。可见,我其实是个没得到过多少善意的人,才会将偶然的奇遇抓得如此紧。
“你谈过恋爱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要不我们试试?”
“……好。”
早在第一次搂住她的肩时,我就已经想好了这段恋情的墓志铭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只不过是在慢慢刻写,而区别在于她是笔,我是墨。我对她而言,不过是一罐可乐。